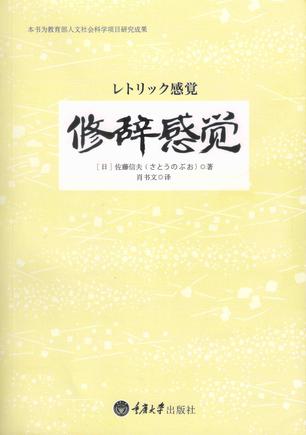
我一直在想,只用一句话,怎样与修辞交心?
一流如张爱玲、鲁迅,他们似乎毫不费力、信手拈来,美妙动人之辞句便从钢笔尖儿,顺着毛糙的纸面,勾连着,汩汩流出来,呼啸着奔涌着,带着一种叫做“文气”的东西,击中了纸面外捧着书的人,读出了百年后一个一个不约而同的心事。
倘若世界毁灭,每个学科都只能留下一句话,物理是一切由原子组成,社会科学是双盲实验,语言学是人类靠隐喻认识世界,——那么修辞则是,修辞以立其感。
创造感觉,发现认识。
语言向来不是孤立的。我们以为,人类在一个沟沟壑壑的大脑里,思绪走了九万八千里,摇摇又摆摆,孤身走上歧路、踏过独木桥、拐入羊肠曲径,寻寻觅觅,终汇入一条万无一失的阳关大道——凭亿兆后人在此驰骋生发,向太阳无尽奔跑。语言落下,为思想盖上钤印,尘埃落定。不,不是这样的。我们把一切想得太完美了。
思想没有尽处,用语言以思考——语言乃思想本身。我思,故我在;我说,故我思。和朋友热火朝天谈天说地,想法会更多。思想从来没说过自己是完美的。进化从来没说过自己是完美的。或有丰硕的奇迹,那是一路上自然造化的馈赏。那是一条归途,没有目的。
「嘿,你在吗?说话呀!」
「嗯,我在。」
「……」
「我一直在。」
只有语言,让你明白思考了些什么。那是一个永远前进的时态。前进,直到死亡,直到毁灭。
而修辞,是语言的思考方式。日出江花红胜火,春来江水绿如蓝,你用火与蓝来思考江边的花、春潮的江水。上善若水,你用水来思考善。半壕春水一城花,烟雨暗千家,半与一,烟雨笼罩下,千家暗淡。思君令人老,岁月忽已晚,我用岁月来思念,当我思念你的时候,岁月忽然纷纷过去了那么多,而我,因之思念,已垂垂老矣。
好修辞,能够复现感觉。回忆会渐渐斑驳,一如容颜老去。感觉却是最容易腐坏,容不得保鲜,下一刻永远与上一刻不一样,或更醇厚,或已酸变。人类在记忆长空中试图抓住流水,即使徒劳,也想试一试。人类总是坚韧的,他们不放弃,便有了洋洋文辞,灿灿诗句。未曾老去斑驳的容颜镌刻在了泛黄的诗句里,记忆里的一颦一笑,折下一枝梅花,斜斜倚着墙,钗头的凤凰将飞欲飞,还有千年以后的伤心人,与自己感怀同样的哀伤。红颜易老。红颜未老。
「嘿,你在吗?说话呀!」
「嗯,我在。」
「……」
「我一直在。」
「天涯明月共此时。」
「伤心同是断肠人。」
那杯千年的浊酒温了又温。从麻纸,到宣纸,道林纸,电子纸……时光漫长无尽,而弹指一瞬。我与修辞交心,毋宁说是与人交心。与君同是伤心人,你我,从来不是一个人。
那时,要交出一篇《修辞感觉》或《修辞认识》的读后感,我在图书馆的阳光里,只读到了120多页,苦着脸,绞尽脑汁。我向来是个跳脱不着调儿的人,却想悬崖勒马,好好写出一篇读后感,努力憋出了这篇读后。回过头,给自己打评价,只能说,小聪明,小文采。
现在,我终于读完了《修辞感觉》,啃的时候觉得佐藤是个典型的中年日本文学教授,一丝不苟又不苟言笑,带着精细的镊子,眼眶里镜片折出了日式柔光,带着皱纹的手,用镊子一点一点拨弄文字。很多修辞手法就生根在日常语言里,甚至于是对日常生活的模仿和再现。我们的耳朵就在修辞中培养语感。谁都不应当拒绝修辞、惧怕修辞。修辞不应当是标本,固定为“生动形象地写出了 XXXX”的答题范式,随着成长“哐当”一声封存在灰暗里。它闪闪发光,眼里有慧黠,眼里有世间万物。